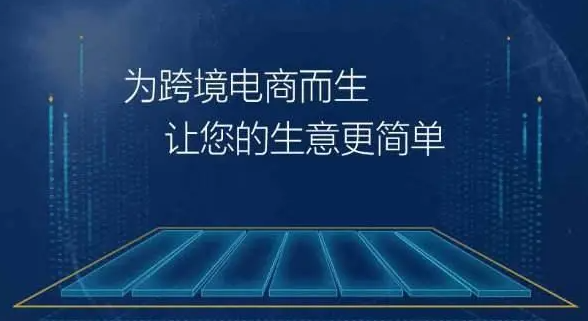青未了|老家的枣树
文/侯凌肖
记忆中,在老家的院子里,有一棵树龄四五十年的老枣树,就生长在东屋南旁,与它相邻比肩的还有一棵老杏树,那时农村有句老俗语:“杏旺人不旺”,后来被父亲刨掉了,于是老枣树便有了得天独厚的生长空间,树干长得有碗口粗,整个树像一把巨大的雨伞,罩着大半个院子。夏日里在树下乘凉、吃饭,很是惬意。
那时,每年到了枣儿成熟的季节,树上都结了很多红枣,红枣个头大,又脆又甜,母亲常叫它“核桃纹枣”。母亲不吝啬,每当收完枣儿总要拿一些枣儿分给左邻右舍,让他们尝尝鲜。再如,街坊邻居孩子办喜事向母亲要干枣,她总是挑选些好的,用花手巾一包,乐颠颠地给人家送去。在我的记忆中,枣树越长越高,树枝修剪了一茬又一茬。由于枣树太高,采摘枣儿十分困难。树矮的枝条,母亲找来一根长竹竿,在竹竿上端绑上镰刀或铁钩子,钩住树枝,用力拉住树枝来回晃动。这时,树枝上的红枣便哗啦啦落下来。每次打枣,不等枣儿全部落完,我和哥哥就迫不及待地抢枣。母亲总是关心地说:“等会捡,小心砸着头!”为了防备红枣砸着头,哥哥把一个水瓢盖在我头上,以防下落的枣儿落在头上。
随着年龄的增长,我和哥哥不再抢枣,而是帮着母亲摘枣。哥哥上树麻利,鞋子一脱,三下两下便爬上了较高的树杈,我和母亲负责在树下捡枣。哥哥在树上选择一个牢固的树叉站好,一边摘了红枣解馋,一边把他周围的红枣一吐噜一个地摘下来,放进挂在脖子上的蓝书包里,随后,双手握住树枝使劲摇晃,枣儿噼里啪啦直往下掉,我在下面高兴的大叫起来“下红枣雨喽”!于是,欢声笑语与枣儿一样在院子里蹦跳飞溅,收获的喜悦与场景,深印在孩提时的记忆中。摇不下来的就用一根细长的竹竿或木棍抽打。一片片叶子被抽打下来,绿色的叶子飘落一地。这时,院子的角角落落都有红枣,连屋顶的瓦缝都有,满院真像下了场红枣“雨”。
母亲每年都晒很多干枣。为了便于晾晒,母亲拿出簸萁、席子等家什放在院子的高处晾晒,剩余的部分枣母亲用针和白线把红枣一个个串起来,然后一串串挂在墙上。为了保鲜,母亲还挑选些好的洗净晾干,先在酒里蘸一下,然后放进黑坛子里,盖上盖子,再用塑料布裹好扎紧。封坛后,放在阴凉处存放,等到了过年时才拿出来吃。经过酒精保鲜的红枣,就像刚从树上采摘的一样,颜色鲜红,味道也美。母亲往往过年时用来蒸花糕。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,从我记事起,每年都能吃到新鲜的红枣。那时,为了改善窝头的口感,母亲挑些青枣和面做成窝头,记得那是用豆面、玉米面做成的,吃起来又香又甜。过年时则吃母亲做的红枣花糕,也是童年最为高兴的事。那时母亲用菜刀把圆形蛋糕一块块切开,往往把最多的枣糕让我享用,母亲疼爱自己的往事记忆犹新,终生难忘。
1978年8月,我接班成为了一名建筑工人。从此,我告别了家乡,告别了老枣树。母亲对老枣树是深有感情的。正是老枣树的无私奉献,给艰难度日的全家人带来了丰盛的果实和无尽的欢乐。此后的几年间,我回故里探望母亲时,她老人家总忘不了让我给老枣树施肥、浇水。往往是春季植树时节。我拿了铁锹,在枣树周围挖了一圈小坑,施上土杂肥,浇上一桶甘甜井水。母亲满脸笑容地看着枣树根部慢慢下渗的水,抬头看看发出嫩芽的老枣树,自言自语道:“吃饱喝足,秋上枣儿会更大、更甜、更多的!”那是母亲对老枣树的期盼和希望。
记得,母亲去世的第六个年头(2003年),那棵经受风雨苍桑的老枣树,因焦梢枯萎而死,它的“离去”让我难过了好一阵子……
投稿邮箱:ddsww2022@163.com
壹点号当代散文
新闻线索报料通道:应用市场下载“齐鲁壹点”APP,或搜索微信小程序“齐鲁壹点”,全省800位记者在线等你来报料!